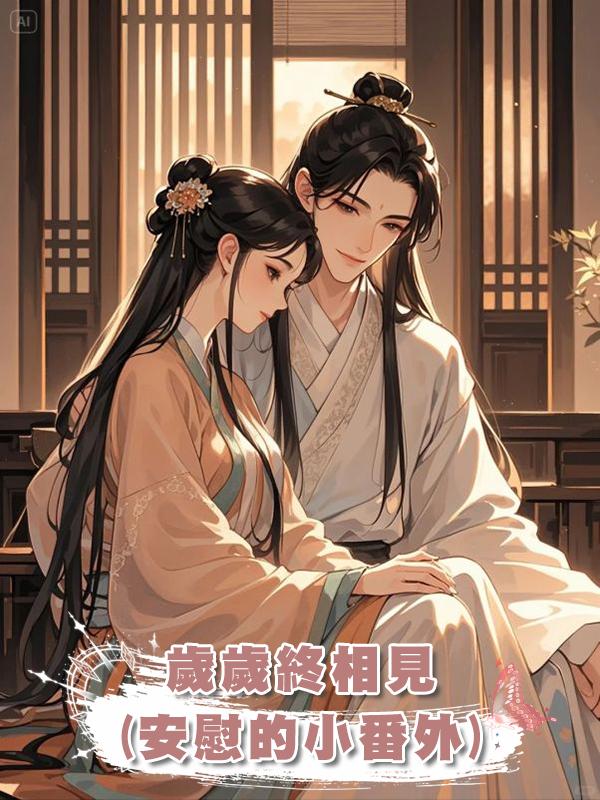與你千般好第4章
“我看是,不然剛才人家放著好端端的座位不要,說坐講臺邊?”
“那也可能是聽說了蘇好把前同桌害休學的事,望而卻步了呀!”
“要我說,還不如坐講臺邊,長這麼張男神臉,又是國家級的競賽苗子,可別成了下一個許芝禮……”
教室外,杜康小聲訓著話:“你這一身火鍋味,又跑哪兒去了?”
蘇好還沒答,他又自顧自擺擺手:“算了先不說這個,剛剛新同學跟我提出坐講臺邊,我就猜你肯定跟人家說了什麼。這事我不允許。別說新同學是好學生,就算差生也不行。我就不喜歡其他班那些風氣,讓搗蛋的孩子坐講臺邊聽課,那地方天天梗著脖子看黑板,對頸椎能好嗎?糟踐人嗎這不是?”
“那糟踐我吧,”蘇好指指那兩盆綠植,“我坐那兒行不行?”
“不行,都是祖國的花朵,怎麼能厚此薄彼?老師知道你本性不壞,不許想過去那些不好的事了,好好跟新同桌相處,聽見沒?”
蘇好嘆息一聲:“那萬一我們處太好了怎麼辦?我當初跟許芝禮鬧掰,主要是同性相斥,現在來了個男同桌,還長得這麼好看,從頭到腳都是我的理想型,我怕自己忍不住跟他早戀。”
“蘇好同學,你要是在學習上也這樣有自信,老師會很欣慰。”
“?”
“早戀這事,一個巴掌拍不響的呀,就算你忍不住,以徐冽同學優良的品質作風,又怎麼可能跟你早戀呢?”杜康安慰地拍了拍蘇好的肩。
“……”
滿教室哄堂大笑。
蘇好在人聲鼎沸裡走進教室,一巴掌拍上門板:“都笑屁啊?”
瞬間滿堂死寂,這一巴掌的殺傷力,比政教主任不差。
蘇好有這個威力,還得從跟陳星風的關系說起。
Advertisement
這位哥家境好,脾氣炸,架打得厲害,從小渾到大,中二時期甚至成了學校叱咤風雲的“扛把子”。
可考上高中,到了南臨以後,陳星風卻慘遭蘇好修理,日常被她踩鞋、踢腚、踹小腿肚,有陣子一看見她就狼狽逃竄。
加之學校裡陸續傳開蘇好如何如何“社會”的流言,後來又出了她帶許芝禮上外邊鬼混,害人家休學的事,這位姐就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繼任“扛把子”。
蘇好回到窗邊坐下,看見自己被杜康扣留的文具袋已經擺在課桌上。不知是杜康放的,還是徐冽。
她轉過頭,瞥了一眼認真翻著書的新同桌。
她的新同桌正拿著一支水筆,在新課本的目錄頁上圈畫標記,大概在劃分哪些是學過的內容,哪些是新的知識點。
整個人冷清到仿佛與世隔絕。
蘇好在座位上放空一會兒,怎麼都不習慣餘光裡多出的那道人影,隻好趴下去睡覺。
結果還沒睡著,刺耳的下課鈴聲就響了起來。
剛才杜康勒令她第一節 晚自修下課後,把徐冽課桌裡的雜物取出來。
她嘆了口氣,從零錢包裡取出一把銀光閃閃的鑰匙,轉過身去:“讓讓?”
徐冽看她一眼,合上課本站到一邊。
南中的教室使用翻蓋式課桌,桌蓋邊緣有個可以上鎖的金屬扣。但為避免學生藏違禁物品,原則上不允許這樣做。
蘇好當然不是遵守原則的人。
她用鑰匙擰開鎖扣,取下掛鎖,一把翻起徐冽的桌蓋,正要伸手往裡掏時,忽然一頓。
課桌裡四散著幾張籤了她落款的素描——
全是人像。
男人的人像。
一絲不掛,肌肉賁張,連某器官都描繪出具象的,男人的人像。
“……”她這金魚腦子,怎麼不記得寒假前在課桌裡塞了這些畫?
蘇好滯住的剎那,徐冽的目光落了下來。
不知道是不是錯覺,蘇好覺得他似乎對此產生了一絲難能可貴的——驚訝?
蘇好用了一秒鍾,在“慌慌張張收拾起這些畫”,和“大大方方讓他看個夠”之間,選擇了後者。
“習慣一下,你同桌我是個思想非常open的藝術生,”她手肘支著桌蓋沿,嘴角的不屑拿捏得恰到好處,“這種尺度都接受不了,我們以後處起來會很困難。”
“哦對了,還有,”蘇好隨意指了指畫上跟徐冽截然不同類型的肌肉男,像在澄清剛才跟老班說的話,“順便介紹一下,我的理想型。”
“……”
徐冽又看了一眼她筆下的器官,用了一秒鍾,在告訴她“按這個尺寸要求,可能這輩子都沒法實現理想”,和“隨便吧”的沉默之間,選擇了後者。
第4章 二月雨
蘇好從徐冽那裡搬走了一堆雜七雜八的物件,胡亂塞進自己課桌,又把佔地方的三角畫架折疊起來,靠去牆角。
第二節 晚自修上課鈴一打,她把頭轉向窗外,繼續睡覺。
這一覺睡得還挺沉,她連下課鈴都沒聽到,不過臨近結尾做了個噩夢,夢到自己不管走到哪裡,都感覺有雙森冷的眼盯著她的背脊。
可等蘇好醒過來,別說背後沒人,整個教室幾乎都已經走空了。
之所以說“幾乎”,是因為她旁邊還有一位——徐冽趴在課桌上,一條手臂枕在額角下,另一條手臂曲起來搭在頸後,睡得比她還沉。
蘇好看了眼腕表,快十點了。
就也沒人叫醒他們?
她抬起酸麻的胳膊,活絡了一下筋骨,用手肘推了推徐冽。
沉睡中的少年驀地睜開眼來,帶著鋒芒的目光銳利上掃,黑漆漆的瞳仁裡滿是戒備。
像一頭被驚擾了眠夢的狼,將要暴起咬斷獵物的喉嚨。
蘇好心髒沉沉一跳。
白天一直靜悄悄的人,這會兒過激的反應倒叫她愣了愣。她恍惚地想,這警覺的樣子,怎麼有點像舊街那些刀尖舔血的混子。
她一定是還沒睡醒。
蘇好抬起一隻手,在徐冽眼前試探地晃了晃:“喂。”
徐冽眨了一下眼,濃密的眼睫扇落兩道陰影,臉上敵意慢慢散去。
他回過神,直起身,喉結輕輕滾動,揉了揉後頸:“怎麼了?”
變聲期末尾,男生的嗓音本就偏低,倦意沒消散的時候又多了一點啞,鑽進耳朵裡帶起沙沙的痒和奇異的酥麻。
“哦,那什麼,”蘇好清清嗓子,也忘了叫醒他是為了把關門鎖窗的累活交給他,“就跟你說,下課了。”
她站起來準備走人,一轉頭卻看到背後多了把椅子,椅子上還放了個泡著枸杞茶的透明保溫杯。
蘇好拍拍徐冽的肩,狐疑道:“這椅子和保溫杯什麼時候在這兒的?”
徐冽扭過頭來看了一眼:“不知道。”
蘇好正回憶在哪見過這個眼熟的保溫杯,答案就自己長腳上門來了——
“醒了啊?”杜康拿紙巾擦著手走進來,大概剛去了一趟洗手間。
蘇好不可思議地指指那把椅子:“老師,你剛一直坐在我背後?”
“是啊,下課過來一看,你倆都睡著,我就坐這兒等啊。不是你讓老師尊重你們的生理需求嗎?”
“你剛才是不是也做噩夢了?”記起徐冽醒轉時的反應,蘇好轉頭問他。
“……”徐冽的沉默說明了一切。
蘇好對杜康攤了攤手:“您看,您完全可以把我們叫醒,您這麼變態地盯著我們,我們這睡眠質量也沒法保證啊。”
“哎,蘇好同學,非常好,已經開始用‘我們’來表達你和新同桌的關系了,而且連用三個!看來老師的話,你有聽進去。”
“……”
蘇好十分懷疑,如果杜康有天粉上什麼CP,一定是那種能帶領所有CP粉從縫裡摳糖的顯微鏡粉頭。
“我回宿舍了。”她一言難盡地跟杜康比個“拜”的手勢。
“等會兒,坐回去。”杜康捧起保溫杯,喝了一口枸杞茶,來到她和徐冽面前,“在這兒等你們,是有正事要說。今天考場上那事,處理結果出來了。”
“秦韻同學已經承認錯誤,老師們商量了一下,該處分是得處分,不過人都有行差踏錯的時候,所以先給她記一次警告,如果到畢業為止不再犯,就給她撤銷的機會,你覺得怎麼樣?”
蘇好眨眨眼:“我跟她又不熟,她以後的人生跟我半毛錢關系沒有,黑她檔案對我有什麼好處?記不記過這事隨便。”
“你這想法就對了,古話說得好,得饒人處且……”
“我要她下周一在升旗儀式上給我道歉。”蘇好把話說完整。
“……”杜康臉色發苦,“道歉肯定是要的,但當著全校師生面,那她以後……”
“怕她在學校受人白眼混不下去啊?”蘇好嗤笑一聲,“心理素質這麼差,就別幹缺德事啊,難道是我逼她誣陷我的嗎?殺人未遂也是犯罪,不能因為被害人防衛得當沒死,就不負法律責任了吧。”
杜康腦袋裡那根弦繃得一跳一跳,張了張嘴,又沒說出話來。
也不怪蘇好咄咄逼人,老實說,他也覺得該讓秦韻公開檢討,誣陷人作弊比作弊本身更惡劣,要不是蘇好頭腦靈光,現在受人白眼的不就是她了嗎?
這汙人清白的事,如果秦韻不當眾澄清,以後三人成虎的流言髒水豈不是還有可能往蘇好身上潑。
“這個事,老師盡量幫你爭取。”杜康捏捏拳頭,換了個語氣,奇怪道,“你這小姑娘,邏輯思維這麼清晰,怎麼還天天考倒數呢?”
“……”無語,這種人身攻擊真的無語。
蘇好忍耐地拿手扇了扇風,把頭撇向窗外,轉眼又記起不對勁:“等等,這事跟他什麼關系,幹嗎叫他旁聽?”她指了指徐冽。
“這就是老師找你們談話的重中之重了。”杜康把保溫杯啪嗒一下擱到徐冽桌上。
敢情您說了半天才到重點?蘇好費解地託起腮,耐著性子繼續聽。
“我問了秦韻同學,誣陷你的那張紙條是從哪來的。她說,是在我們班門口走廊垃圾桶邊撿到的。我又去問坐在你前面的郭照同學,她說早上把寒假作業遞給你以後,那紙條就隨地丟了。”
“我一想,這不能啊,我們班同學這麼懶,衛生都打掃不幹淨,在地上撿到垃圾,不扔到教室裡的垃圾桶,還特意跑去走廊丟?而且秦韻同學如果是偶然撿到,怎麼就那麼確定那是你的字跡?”
蘇好點點頭。
分析得有理有據。雖然她早就想到了。
“所以啊,也不知這事是不是還有其他人參與。雖然老師常說同窗之間要友愛,但現在個別同學……”杜康嘆了口氣,沒往下說,“總之老師給你提個醒,事情沒弄清楚之前,多注意一下身邊。”
他說到這裡看向徐冽:“徐冽同學當時剛到學校,是班上第一個能擇幹淨的人,所以在這件事上,老師最信任的就是你,希望你最近也替老師留意一下。”
“除了像今晚這樣的考試期間,蘇好同學平常晚自修大多在藝術館畫室。要是發現有人趁她不在搞小動作,你能幫就幫一把,也把情況及時反饋給老師,好嗎?”
徐冽點了一下頭。
“行,那你們趕緊回宿舍吧,”杜康揮揮手打發兩人,“關門鎖窗我來。”
*
因為杜康慷慨的目送,蘇好沒能從課桌裡掏走手機就回了宿舍。
南中宿舍樓歷史悠久,裡外都已有些老舊,住宿條件很一般,連獨立衛浴都沒有。
高一高二的宿舍隻設上下鋪,不設課桌椅,到點熄燈,不許學生打手電。
學校的意思是,頭兩年還是身體為重,可以早睡早起去教室學習,但別熬夜。反而不少學生家長幹著急,有條件的都把孩子接回去走讀。
所以南中高一高二住宿率常年達不到三分之一。尤其像蘇好這樣的準高三,這學期開學後又搬走了一批。
熱門推薦
為了賺錢,我在網上做戀愛咨詢師。 接到了死面癱老板的單。 追的還是我自己! 我勸他:「你們沒緣分,她的老公另有其人!」 後來,他把我堵在墻角:「老婆,另有其人是什麼意思?」
室友喝多以後,以我男神的名義在表白牆上實名發了表白我 的話。不隻是表白,還給我一頓吹捧,十足的舔狗語氣。第 二天酒醒,我們全都驚呆了。
撿到厲鬼冥婚紅繩,我反手系在了山神像上。我剛要走,耳 邊聲音響起:「平時不上香,有事找我剛?」路邊那條紅繩 不好看。但它捆著的百元大鈔很好看。
"我替姐姐和親,嫁給年過半百的大單 於。紅面紗揭開,映入眼中的卻是一張 年輕面龐,臉頰上滿是血滴。「我可"
修竹茂林中,雨水淅淅瀝瀝打在綠竹葉片上,又垂墜落入泥 濘中。竹林中,兩三抹模糊的身影若隱若現。
周溪並不愛我,她嫁給我的條件是,一旦她的初戀回來了,我們就要立刻離婚。 結婚十年,我寵了她十年,而她等了十年。 終於,她的初戀回來了。 一紙離婚協議書丟在了我面前。 我咳著血,釋然地簽了自己的名字。 周溪,你的恩情我還完了,我該走了。
- 主題模式
- 字體大小
- 16
- 字體樣式
- 雅黑
- 宋體
- 楷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