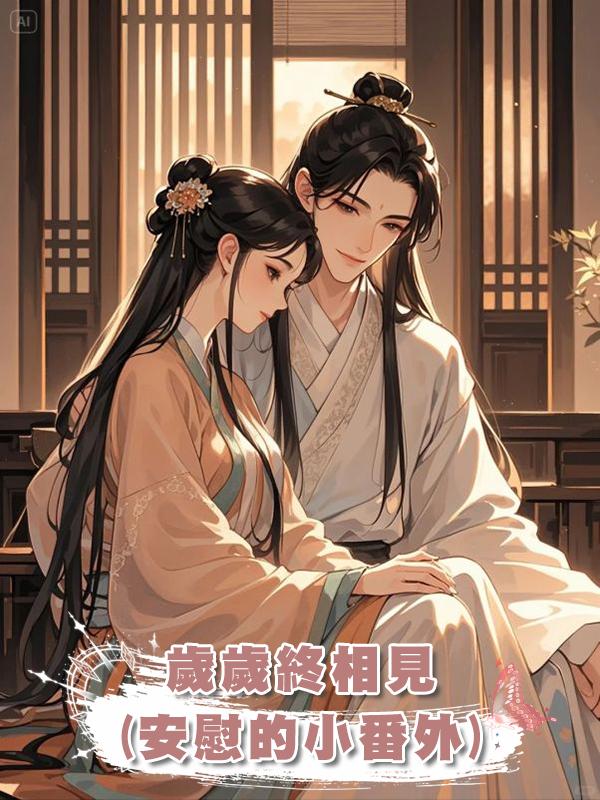與你千般好第76章
“是。”鄒月玲笑了笑。
杜康見她笑容裡帶了些欲言又止的意思,問道:“怎麼了蘇好媽媽,您這邊是有什麼顧慮嗎?”
鄒月玲沉默片刻,嘆息著點了點頭。
月初的時候,蘇好跟她說不去美國了,她起初以為女兒還是在顧忌她,所以拿出了心理醫生的診斷報告。
報告顯示她這三個多月的治療已經初步取得成效,她也跟蘇好說,她和爸爸已經商量好了,決定兩人一個留北城繼續照管生意,一個到美國陪讀,剛好順帶拓展外貿業務,總之算是解決了蘇好所有的後顧之憂。
但即便如此,蘇好依然說自己不想去美國了。
雖然很惋惜,但她和丈夫當然會尊重女兒的決定,隻是心裡不免疑問,女兒為什麼放棄這麼難得的機會,百般試探問不出究竟,這才想來趟學校問問班主任。
鄒月玲把這件事的始末跟杜康簡單講了講。
杜康聽完瞬間陷入了沉默。
“杜老師,您是不是知道原因?”鄒月玲著急地問。
杜康皺著眉頭:“這……蘇好媽媽,您別急,不確定的事我不好盲目說,我想我需要先找蘇好聊聊。”
他話音剛落,身後辦公室的門再次被篤篤篤敲了三聲。
杜康和鄒月玲齊齊轉過頭去,看見了徐冽。
鄒月玲望著徐冽的臉愣住,腦海裡一下子浮現出五一假期百貨商場門口的那一幕——蘇好跟她介紹說,這是愷愷的家教老師。
她打量著徐冽這身高中生校服,詫異地站了起來。
*
Advertisement
晚上七點,蘇好坐在舅舅家客廳沙發,第十八遍看腕表。
鄒月玲和蘇文彬昨天跟她發微信消息說,他們今天傍晚會到舅舅家接她,順便留下吃頓晚飯。她以為吃過晚飯之後大概就會回自己家,應該見不到徐冽了,沒想到爸爸傍晚給她打了個電話,說他們臨時有點事,晚點再來接她。
她心想那說不定還能跟徐冽碰上一面,一直盼著七點到來,結果盼到現在,一向準時的徐冽都沒到。
窗外雷聲已經轟隆隆地響過好幾陣,她不方便給徐冽打電話,怕雷雨天外邊不安全,隻能繼續等,等到又一聲驚雷過後,傾盆大雨哗啦啦潑了下來。
蘇好驀地起身,站去了窗前,望著電閃雷鳴的天,心裡隱隱有些不安。
旁邊林闌也在念叨:“哦喲,怎麼這麼大的雨,也不知小徐到哪了,這得出去接他一下啊。”
屋裡話音剛落,門鈴響了起來。
蘇好緊張之下走漏了心思,比林闌更快一步衝了過去,一打開門,看到徐冽拎著一把湿淋淋的傘站在外面,頓時松了口氣。
也因此,她錯過了徐冽眼底那一絲閃爍。
“小徐啊,辛苦你雷雨天還過來,有沒有淋湿啊?”林闌迎了出來。
“沒有,”徐冽收起傘,走了進來,換好鞋,對林闌笑了一下,“林阿姨,剛才蘇好跟我說,她的畫隻差個結尾了,讓我今天先給她畫畫,您看方便嗎?”
蘇好一愣,不明所以地看著徐冽。畫確實隻差一點點就完工了,那是因為她想拿畫畫這件事當借口,跟徐冽繼續在閣樓“幽會”,所以很久之前就緩了畫畫進程,一直沒作結尾。
但她剛才根本沒聯系過徐冽。
林闌也是滿臉疑問:“剛才?”
“啊,對,”雖然不知道徐冽想搞什麼,蘇好還是趕緊圓場,“之前為了方便排畫畫時間,我跟徐老師交換過微信。”
林闌心裡隱約覺得有點古怪,但又一時講不上來古怪在哪裡,說著場面話:“哦,是這樣,沒事沒事,那你們先上去畫畫,反正愷愷剛好還在吃水果。”
徐冽朝林闌點點頭,跟蘇好一起上了閣樓。
蘇好被他這突如其來的一出驚出一身冷汗,到了頂樓悄聲罵他:“你這一聲招呼不打的是想幹嗎,差點露餡了!都混一個學期了,你想晚節不保嗎?”
徐冽默不作聲地把她拉進閣樓,走到窗前。
蘇好看著他結了霜似的表情,一頭霧水:“你怎麼了?”
窗外暴雨如注,隔著窗,雨滴打下來的聲音好像蒙在一層鼓皮裡,厚重又沉悶。
徐冽凝望著這場瓢潑大雨,沉默片刻後,轉過頭看蘇好:“你拿到加德裡的預錄取了。”
蘇好一愣,飛快搖頭:“沒有啊,你從哪聽來的小道消息?”
徐冽皺起眉,垂眼注視著她:“不要騙我。”
蘇好喉嚨底哽了哽,嘴上依然若無其事:“真沒有,拿到預錄取我還不高興上天了!拿不到的啦,他們油畫系要求超高的。”
“那如果拿到了呢,去嗎?”
蘇好繼續搖頭,笑著說:“我不都跟你說了我家裡的情況嘛,我爸媽不放心我,就算拿到了我肯定也不會去。”
徐冽緩緩沉出一口氣,撇開頭望向窗外。
窗外依舊雷聲隆隆。
蘇好忽然沒來由地心慌。
死寂般的靜默將時間一分一秒拉長。
許久後,徐冽收回視線,重新看向蘇好:“我見過你爸媽了。”
青紫的閃電晃亮天空,轟一聲巨響,像直直打在人頭頂。
蘇好渾身的血液仿佛在這一刻凝固,垂在身側的手使勁一攥,卻好像什麼也沒攥住。
“蘇好,別這樣,”徐冽伸出雙手,輕輕捧住了她的臉,額頭貼上她的額頭,再出口時聲音裡多了一絲顫抖,“求你不要這樣。”
第62章 七月雨
這個夜晚讓徐冽想起了四年前的那個盛夏。
四年前, 也是這樣一個雨夜,他去大學裡找暑期留校實踐的姐姐,在畫室外意外聽到了姐姐跟閨蜜的對話。
閨蜜問姐姐, 你這設計稿也太敷衍了,這實踐項目不是跟你們學院出國交換名額掛鉤嗎, 你就不爭口氣?
姐姐說爭什麼氣, 當一隻漂亮的花瓶不好嗎?
閨蜜又問姐姐,那你這是準備把家業拱手讓給你弟了嗎,你後媽成天捧殺你,你甘心?
那是當時尚且年幼的徐冽第一次認識到“捧殺”這個詞。
雖然他跟姐姐是同父異母, 但從他記事以來, 印象中, 媽媽一直將姐姐視如己出。甚至相較對他的嚴厲,媽媽反而對姐姐噓寒問暖更多,幾乎對她百依百順,把她寵得無法無天。
而姐姐對待媽媽也像對待生母一樣親昵。
他無法相信, 這麼多年,自己看到的全都是假象,直到聽見姐姐的回答——
一個後媽, 還真指望人家視你如己出?面上疼你寵你就得了吧,不過私心給兒子爭點家產, 也不是多大仇,反正我又沒興趣當女強人,我不要的東西, 她要就拿去咯。大家在一個屋檐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,非爭得你死我活,把一家子攪得烏煙瘴氣,多不舒服?
然後他明白了,媽媽是望子成龍才對他百般嚴苛,是想養廢姐姐,才放任她吃喝玩樂不學無術。
從那天起,媽媽這個詞就在他心裡慢慢崩塌了。
可是他的媽媽依然會在他生病的時候擔心得整晚無眠,半夜心急忙慌送他去急診,到醫院才發現自己穿了兩隻不一樣的拖鞋。
她不是一個善良的後媽,但她很愛自己的兒子,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。
所以他甚至沒有立場去責備媽媽。
他站在天平的中間,無法改變媽媽,也無法說服姐姐,最後隻能繼續維持現狀,維持這個家的虛假繁榮,默認了姐姐的犧牲。
四年前,他已經欠姐姐一個夢想,四年後,當他從蘇家人口中得知蘇好放棄了什麼,他再也不想有人為他讓步。
所以他跟她說:“求你不要這樣。”
雨還在下,玻璃窗在狂風中噼啪作響,仿佛隨時都要碎裂。
徐冽捧著蘇好的臉,與她額頭相貼,漸漸感覺到有湿潤從她臉頰蜿蜒落下,落進他的掌心。
蘇好顫動著眼睫,耳邊不斷回響起那天教學樓天臺上,許芝禮跟她說的話。
——後來很多個晚上,再動起那種念頭,我就會想起這句話,至少不是今晚。
——然後就這麼過了一晚又一晚,一晚又一晚……我發現,如果不是今晚,也許就真的不會是明晚了。
——可是蘇好,你說,他是怎麼知道這個道理的呢?
徐冽是怎麼知道這個道理的呢?
如果不是經歷過同樣的夜晚,他怎麼會知道這個道理。
蘇好不是為了談戀愛才放棄出國,她是因為害怕。
害怕她走後,徐冽又會變得沉默寡言,變得獨來獨往,會被那些不該他背負的詛咒和謾罵打垮,變成第二個從前的許芝禮,變成第二個當初的蘇妍。
她曾經活在追夢的世界裡失去了姐姐。
現在她想當徐冽的太陽。
蘇好搖著頭,哽咽道:“可是我害怕……”
她沒說她害怕什麼,徐冽卻好像已經懂了。
他拉遠了一些與她的距離,讓她可以看清他的眼睛:“不用怕。”
“嗯?”蘇好抽噎了下。
“你見過誰害怕太陽太遠嗎?”
茫茫宇宙隻有一個太陽,卻已經足夠讓這個世界萬物生長。太陽是不需要靠近誰的。
隔著萬裡重洋,她一樣是他的太陽。
一樣能讓他汲取到光亮。
*
蘇好沒有立刻回應徐冽,不管作什麼打算,她都需要時間考慮,這也是情理之中。
雨停了,鄒月玲和蘇文彬把蘇好接回了家,讓她好好整理心情。
蘇好離開後,徐冽在鄒家上完了最後一堂家教課。
林闌已經從鄒月玲口中得知徐冽的真實身份,心情五味雜陳之餘,不管多喜歡徐冽,也沒道理再讓一個高中生繼續打工,所以給他結清了工資。
徐冽從鄒家離開,回到學校已經是晚上十點多,走近校門時,看見那裡停了一輛黑色賓利。
他被迎面打來的車燈刺了眼,抬手擋了一下,司機立馬熄了車頭的遠光燈。
副駕駛上下來一個西裝革履的男人。
“徐小公子,”男人叫了他一聲,步履匆匆上前來,臉上微露焦色,“您還記得我吧,我是程總的特助,高瑞。”
徐冽眯起眼,看著他點了點頭,又看了眼他身後這輛車。
“您手機關機,我就在這邊等您,是這樣的,您現在可能得跟我去一趟北城……”高瑞在社交場上見慣風浪,一張嘴皮子向來能說會道,從沒有一刻像此刻這樣,連組織語言都覺得困難,“徐夫人……我是說,您母親她……”
徐冽的唇抿成平平一線,繃緊了身體。
“您母親今天乘坐紐約到北城的航班,落地北城機場後,跟一行人起了肢體衝突……”高瑞描述著前因後果,試圖衝淡這件事對一個十七歲少年的衝擊,但不論怎樣繞遠,最後還是避無可避,“過程中意外撞傷頭部,現在正在手術室搶救……程總讓我來接您。”
*
凌晨四點半,北城。
醫院重症監護室外,徐冽站在走廊上,望著監護室小窗裡透出的模糊燈光,面無表情地倚著牆。
熱門推薦
為了賺錢,我在網上做戀愛咨詢師。 接到了死面癱老板的單。 追的還是我自己! 我勸他:「你們沒緣分,她的老公另有其人!」 後來,他把我堵在墻角:「老婆,另有其人是什麼意思?」
室友喝多以後,以我男神的名義在表白牆上實名發了表白我 的話。不隻是表白,還給我一頓吹捧,十足的舔狗語氣。第 二天酒醒,我們全都驚呆了。
撿到厲鬼冥婚紅繩,我反手系在了山神像上。我剛要走,耳 邊聲音響起:「平時不上香,有事找我剛?」路邊那條紅繩 不好看。但它捆著的百元大鈔很好看。
"我替姐姐和親,嫁給年過半百的大單 於。紅面紗揭開,映入眼中的卻是一張 年輕面龐,臉頰上滿是血滴。「我可"
修竹茂林中,雨水淅淅瀝瀝打在綠竹葉片上,又垂墜落入泥 濘中。竹林中,兩三抹模糊的身影若隱若現。
周溪並不愛我,她嫁給我的條件是,一旦她的初戀回來了,我們就要立刻離婚。 結婚十年,我寵了她十年,而她等了十年。 終於,她的初戀回來了。 一紙離婚協議書丟在了我面前。 我咳著血,釋然地簽了自己的名字。 周溪,你的恩情我還完了,我該走了。
- 主題模式
- 字體大小
- 16
- 字體樣式
- 雅黑
- 宋體
- 楷書